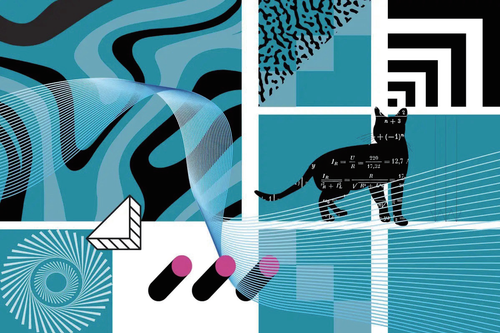100年来,量子理论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奇异得难以言喻的微观世界。但如今,一些大胆的新诠释与实验,或许将帮助我们最终领会其真实的含义。
量子力学的问题,或者说连物理学家都难以理解它的原因,并不在于它描绘了一个陌生的现实图景。由基本粒子构成的世界——一个我们从未直接体验过的领域——与我们感知到的世界截然不同,这一点并不难接受。
问题在于,它没有描绘这两个世界之间的“过渡地带”,没有清晰地勾勒出一个世界是如何从另一个世界中产生的。其结果是,哪怕这幅科学杰作早已完成了一个世纪,我们仍然不知道它对于我们理解现实意味着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并不缺乏想法。至于你倾向于哪种解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品位问题,或者至少是一个哲学问题,因为它们往往无法通过实验检验。正如物理学家大卫 · 默明(N. David Mermin)打趣说的那样:“新的诠释每年都会出现,但从未有哪一个彻底消失。”
不过,过去十年间情况有所改变。量子理论的一个新的转折点是首次提出了明确的观测预测,为实证研究带来了希望。与此同时,另一种理论则因其似乎能一举解决多个令人困惑的量子谜题而备受关注——尽管它意味着“客观现实”或许根本不存在。
更令人振奋的是,物理学家甚至开始尝试通过新方法检验这些假设的有效性。当他们将令人眼花缭乱的思想实验变为现实世界中的测试实验时,我们或许终于能够在理解量子理论含义的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缩小可能性的范围了。”澳大利亚昆士兰格里菲斯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埃里克 · 卡瓦尔坎蒂(Eric Cavalcanti)如是说。
量子理论
20世纪20年代中期,量子力学的发展彻底颠覆了人类长期以来对宇宙运行方式的直觉认识。自艾萨克 · 牛顿(Isaac Newton )在17世纪提出他的运动与引力定律以来,物理学家一直采用一种固定的方式来构建理论:设定一个物理系统,然后用一些方程来预测它随时间如何变化。
但经典力学无法描述电子、光子等亚原子粒子的行为。实验显示,这些粒子能做出各种怪异的行为——表现得像波一样,并且似乎可以同时处于多个可能状态的“叠加态”中。只有当你去测量它们时,它们才表现出确定性的属性。
薛定谔方程捕捉到了这种模糊性,它引入了一个叫作“波函数”的数学概念来表征所有可能的观测结果。这使我们可以计算出粒子在被测量时出现在特定位置的概率,此时波函数被认为“坍缩”了。但它无法告诉我们某次测量的确切结果。换句话说,在测量之前,我们只能知道各种可能结果发生的概率。
测量之前发生了什么?量子理论没有说明。它也没有说明什么才算是“测量”。它甚至没有告诉我们,波函数(通常也被称为“量子态 ”)是否真正代表了物理现实。对于这样一套备受推崇的理论而言,未知之处实在太多了。但归根结底,它们都可以被归结为一个深刻的问题:我们看到的可预测的宏观世界——其本身也由原子和粒子构成——是如何从这个虚无缥缈的量子幽境中产生的?物理学家称之为测量问题,它仍然是量子力学的核心谜题。
哥本哈根诠释
教材中给出的答案是“哥本哈根诠释”——得名于这个解释诞生的丹麦城市。它认为,在粒子被测量之前,我们对其状态一无所知。这在数学上是可行的,因此“闭嘴计算就行”(默明的另一句名言)。但哥本哈根学说从一开始就饱受争议,阿尔伯特 ·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就曾对量子世界明显的概率性质提出过著名的抨击,并坚称“上帝不掷骰子”。
许多物理学家至今仍觉得哥本哈根学说是敷衍的。“它并不是一个对现实本质的严肃回答,”德国图宾根大学理论物理学家罗德里希 · 图穆尔卡(Roderich Tumulka)表示,“我们想要的是关于现实本质的明确陈述。”这种解释似乎也留下了一个看似荒谬的想法——正是我们这些进行观测的人类,也就是具备意识的个体,才“促使”波函数坍缩。
图穆尔卡等人倾向于将波函数看作现实本身的一部分,即无论我们是否观测,它都真实存在。其中最有名的解释是“多重世界诠释”,它认为波函数中包含的所有可能结果都会在测量时得以实现,每种结果都在一个独立宇宙中呈现。
但也有人提出“客观坍缩理论”,它认为量子力学尚不完整,需要在薛定谔方程的基础上加上某种机制,来解释波函数为何以及如何发生坍缩。“这种解释与标准诠释的(关键)区别在于:波函数的坍缩并不是在测量过程结束时神奇地发生的,而是整个动力学过程的一部分。”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大学理论物理学家安杰洛 · 巴锡(Angelo Bassi)说。
近年来,坍缩理论赢得了比大多数理论更多的关注,部分原因是它们为经典现实如何在不涉及人类观测者的情况下出现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按照这种理论,我们之所以看不到像画框或画笔这样的大型物体处于叠加态,是因为坍缩过程的运行机制——相互作用的粒子越多,坍缩就越容易发生。
究竟是什么引发了这种持续的坍缩,目前还不完全清楚。有的模型没有说明,有些则认为是引力。但巴锡认为,这最终可能也没有好的答案——它可能就是自然界的一种属性。“这就是我喜欢坍缩模型的原因,因为它们试图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全新世界的大门——一个我们尚无法理解的、超越量子力学的世界。”
然而,真正让坍缩模型与众不同的是:它们可以被实验检验。它们给出了一些和标准量子力学不同的明确观测预测。例如,这种自发坍缩的恒定过程应该会导致量子粒子不停地晃动,进而释放出多余能量——哪怕信号非常微弱,理论上它也应该能被检测到。
检验量子诠释
在过去的十年里,巴锡与世界各地的同事们一起开展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实验项目,旨在寻找这样的信号。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重新利用本来用于探测暗物质或“幽灵粒子”中微子的探测器,例如意大利格兰萨索山丘地下深处的超灵敏仪器。实验结果正在悄然产生。在2020年,包括巴锡与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所的实验物理学家卡特琳娜 · 库尔切阿努(C?t?lina Curceanu)在内的一个研究小组,就排除了一个“由引力导致坍缩”的最简单模型。
类似实验仍在持续进行中,每一次新的分析都为我们带来新的约束条件,以确定这些模型中哪些可能是有效的。不过,虽然我们终于有机会通过实验排除客观坍缩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目前还没有检测到信号,但这只是开始。”巴锡说。
如果我们真的探测到了一个大家公认的可以支持“客观坍缩”模型的信号,那它无疑足以赢得诺贝尔奖。但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马格达莱娜 · 齐赫(Magdalena Zych)指出,这是否能立即揭示量子理论的真正含义,则是另一回事,因为我们还必须弄清环境中发生坍缩的是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可以解决测量问题,如果你相信量子理论确实缺了点什么,那么这就是你要找的答案。”齐赫说,“但它并不真正揭示量子力学对现实的含义,因为你仍然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人为地赋予它意义,你得说清楚环境中(使波函数坍缩) 的噪声到底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齐赫指出,我们仍无法解释为什么量子粒子的可观测性质会以概率的方式从测量行为中浮现出来。“这才是所有这一切的真正深层谜团,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用概率来描述一切。”她说。没有任何显而易见的理由可以说明,亚原子粒子的行为为什么不能受确定性法则的支配。而它们不能这一事实本身就需要一个解释。
量子贝叶斯主义
在齐赫看来,真正正面迎战这个难题的是另一类量子理论诠释。巴锡和图穆尔卡等人坚持认为量子态是真实的,而一些物理学家则持截然不同的观点:量子态根本不代表独立的现实。
这类诠释中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量子贝叶斯主义”(QBism),它建立在由18世纪神学家托马斯 · 贝叶斯(Thomas Bayes)所创的概率解释体系之上。
通常,我们以“频率主义”的方式看待概率:我们计算多次抛掷硬币的结果,得出正面或反面向上概率均为50%的结论。类似地,对粒子的多次测量就能得出它在被测量时处于一种状态或另一种状态的相对概率。相比之下,贝叶斯方法认为概率是一种主观值,会随着新信息的获得而更新。
根据这一观点,QBism理论的核心论点是量子力学同样具有主观性。它就观测者在进行测量时应该相信什么提出了建议,并允许观测者根据新的实验结果更新这些信念。“它是一套供观测者导航世界的理论。”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鲁迪格 · 沙克(Ruediger Schack)说。他与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的克里斯 · 富克斯(Chris Fuchs)共同发展了QBism理论。
这种解释的魅力在于,它似乎能同时解决多个量子难题。它通过赋予甚至要求主观经验发挥核心作用来解决测量问题。沙克认为,波函数的神秘坍缩只不过是观测者在测量时更新自身信念的过程。
与此同时,QBism理论针对经典现实如何从量子迷雾中产生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是,它是我们对世界的行动,以及我们不断更新对它的信念的结果。这个想法甚至轻松化解了著名的“维格纳之友悖论”,这是物理学家尤金 · 维格纳(Eugene Wigner)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一个思想实验。其核心是:它表明两个观测者——维格纳和一个观测他对量子系统进行测量的朋友——可以对现实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体验。
但对于“量子贝叶斯主义者”(QBist)来说,并不存在悖论,因为每个测量结果都是观测者自身体验的一部分。因此,QBism理论彻底否定了“可以从第三人称视角客观描述宇宙”的想法。沙克说,这正是它的核心立场,也是量子力学的最伟大教训:现实是无法仅靠第三人称视角捕捉的。“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其他人则认为 QBism理论难以接受。例如,巴锡就表示,放弃“客观现实”这一代价实在太大。“物理学的意义在于以客观的方式描述自然。”他说。另一个问题是,QBism 理论似乎并没有提供与标准量子力学不同的可观测预测,也没有现实可行的实验验证路线。“说服人们可能只能靠指出其他理论的不足之处。”沙克坦言道。
可以说,我们又回到了起点。如果我们最有希望从经验上解决测量问题的诠释即便被证实,也仍旧无法回答所有问题,而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替代解释却无法被检验,那么我们该何去何从呢?
实验形而上学
不过,我们或许仍有理由保持乐观。在过去几年里,一些物理学家已经开始证明,构成我们对量子理论意义理解基础的前提假设——这些通常被归为形而上学而非科学领域的东西——实际上也可能被纳入实验检验的范畴之内。他们称为“实验形而上学”。“这种方法试图明确不同量子诠释背后的形而上学假设。”卡瓦尔坎蒂说。他是该领域的重要推动者之一。这些前提包括:观测事件的绝对性(即测量结果对所有观测者都是一样的)、选择自由(即测量结果不是由某些测量相关因素决定的),以及局域性(即自由选择不能影响远处或过去实验中的结果)。“单独来看,这些前提可能无法被检验,但合在一起就可以。”卡瓦尔坎蒂说。这种方式或许能排除某一类量子诠释。
卡瓦尔坎蒂是迄今为止利用这种方法进行最有力演示的团队成员之一。2020 年,他和他的同事们利用光子进行了一次升级版的“维格纳之友”思想实验,其中还涉及了“纠缠”现象——一种能让粒子在远处仍保持关联的量子特性。简而言之,他们发现,如果标准量子力学是正确的(例如,没有发现客观坍缩的信号),我们就必须放弃这些假设中的一个:局域性、选择自由或观测事件的绝对性。
这对物理现实施加了迄今最严格的约束条件。卡瓦尔坎蒂说:“如果你想保留‘选择自由’与‘局域性’,那你就必须放弃‘观测事件的绝对性’假设。”而这正是QBism理论所坚持的观点。因此,尽管我们还不能说QBism理论或其他诠释是思考量子力学意义的正确方式,“但我们现在可以缩小可能性的范围了”。
现在,他想更进一步。在2020年的实验中,卡瓦尔坎蒂和他的同事们用光子探测器代替了维格纳本人,并用光子来模拟“他的朋友”。然而,光子显然与维格纳在 20世纪50 年代想象的人类观测者相去甚远,大多数人可能会说光子不算观测者。由于量子态的脆弱性,要让一个由几千个原子组成的分子保持叠加状态是非常困难的,更别提复杂如人类了。但是卡瓦尔坎蒂和他的同事们提出,有朝一日我们也许可以用大型量子计算机上运行的先进人工智能算法做同样的实验,在模拟实验室中进行模拟实验。他说,这可能会告诉我们是否真的必须放弃我们珍视的“客观性”观念,尽管离真正实现这种实验还很遥远。
量子引力
那么,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们对量子力学究竟揭示了什么样的现实,还能期望得到一个明确答案吗?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与量子力学创始人当年为其意义争论不休的状态并无太大差别。“我们目前唯一确切知道的是,某种经典的世界观已经失效。我们可以用数学和实验证明这一点,就像我们知道科学中的任何事情一样。”卡瓦尔坎蒂说。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根据自己的理论思考来决定,在对量子力学含义的各种诠释中,哪一种更有吸引力:你是否准备放弃一种或另一种假设?反过来,你愿意为保留你最珍视的假设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卡瓦尔坎蒂指出,在理想情况下,我们可以从寻找“量子力学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如何相容”的尝试中获得指引。广义相对论将引力描述为质量扭曲时空的结果。他说,如果某种特定的解释能帮助我们在这方面取得进展,那将是一条强有力的线索。“我认为这些基础实验是相关联的,” 他说,“因为‘事件是否绝对’这个问题,对建立一个可行的量子引力理论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我们至少已经开始用我们能够理解的术语来解释量子力学提出的问题,并设计实验来缩小可行理论的范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努力寻找更复杂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点,卡瓦尔坎蒂说:“我认为,当我们用多种方式来看待世界时,对世界的理解不可能比原来更少。”
资料来源 New Scientist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丹尼尔·科辛斯(Daniel Cossins)是一位自由撰稿人,曾在《新科学家》任职九年,最后担任专题编辑负责人。他拥有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历史学学士学位及历史研究硕士学位。科辛斯主要关注自然科学,尤其是宇宙学、粒子物理学与凝聚态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