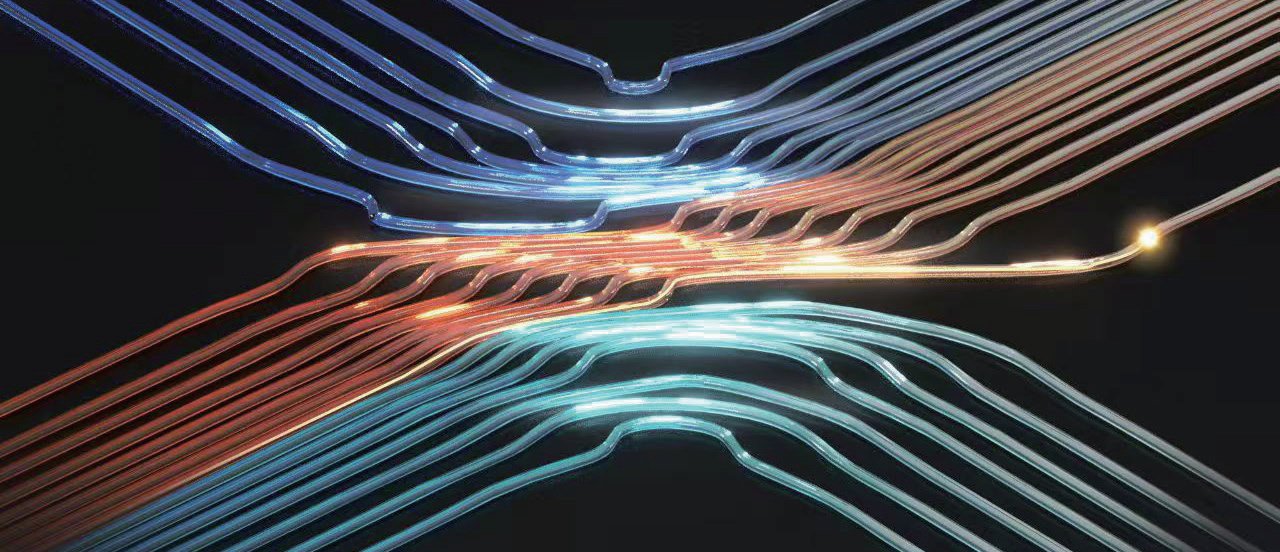路漫漫其修远兮:驳斥ESSW思想实验,实证玻姆轨迹的非局域性
人们想知道玻姆轨迹是否真实存在。1992年,贝特霍尔德-格奥尔格 · 恩格勒(Berthold-Georg Englert,现任北京理工大学讲席教授)、马兰 · 斯库利(Marlan Scully)、乔治 · 苏斯曼(George Süssmann)和赫伯特 · 瓦尔特(Herbert Walther)在《超现实玻姆轨迹》一文中提出了ESSW思想实验。他们考虑一个粒子经过两个狭缝,每个狭缝旁都有一个路径探测器。这种探测器非常特殊,它几乎可以在不对粒子运动产生扰动的情况下,记录粒子经过了哪条狭缝。ESSW经过理论分析,得到一个看似矛盾的推论:当粒子的玻姆轨迹穿过狭缝1时,路径探测器却显示粒子穿过了狭缝2。他们认为这可以证明玻姆轨迹不是物理上真实的,而是“超现实的”。
这一严重的指控引发了长久的讨论。仅仅在一年后,物理学家们就在论文中展开激烈辩论。1993年6月,德特勒夫 · 迪尔(Detlef Dürr)等人凭借《关于“超现实玻姆轨迹”的评论》一文首先发起了对ESSW观点的抨击。作者指出,在玻姆力学的框架下,粒子的轨迹和探测结果必须一致,因为轨迹本身就是定义路径的依据;路径讨论的物理意义本就是玻姆力学(而非正统量子诠释)所赋予的——正是在玻姆力学中,粒子轨迹才是物理实在,路径问题才有明确答案。作者进而指出所谓的“超现实”只是人们对于玻姆力学的误解。在文中,迪尔等人暗示ESSW的思想实验具有荒谬感:“引言部分以提出‘一项关键实验’作为结尾,声称‘根据我们的量子理论预测,该实验将清晰证明玻姆轨迹所被赋予的实在性更多是形而上的,而非物理的’。然而,基于‘提出无意义实验的科学家,其建议不可轻信’这一原则,这一提议反而使论文自相矛盾:作者自己已承认‘量子理论预测’与玻姆力学的预测完全一致。因此他们理应意识到,自己希望用以否定玻姆力学的实验结果,恰恰是玻姆力学本身所预言的结果。在此情形下,资助机构若选择节省经费,倒显得明智了!”
很快在当年10月,ESSW撰写《回复关于“超现实玻姆轨迹”的评论》一文,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他们坚持,玻姆力学虽数学自洽,但其轨迹与实验探测的粒子路径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缺乏物理意义。他们将玻姆轨迹与历史上的“以太”概念进行类比,认为其“实在性”仅停留于理论层面。在结尾,ESSW引用了玻姆的学生亚基尔 · 阿哈罗诺夫(Yakir Aharonov)1987年在《玻姆理论中的回溯性问题》一文的话:“玻姆1952 年开创性的隐变量理论经常被指责为人造的和粗糙的。毫无疑问,对它在这两方面的指责都不无道理。”不过笔者发现,阿哈罗诺夫还有后半段:“但若止步于此,那就完全错失了问题的关键。玻姆在他的理论中追求的,并不是精致优雅,也不是自然性;他真正的意图,是构建一个无论在其他方面如何,至少在逻辑上具有清晰基础的理论。正是因为这种逻辑上的清晰性,玻姆的理论才广受高度而正当的赞誉。”无论怎样,ESSW认为他们已经很好地证明了玻姆轨迹的人造性。至于经费资助问题,ESSW也予以回击,暗示迪尔等人的嘲讽仅仅出自对玻姆力学的主观拥护:“资助机构被明智建议支持那些探索或即将探索量子理论‘反直觉现象’的实验。试想一个(看似牵强的)情景:实验者发现光子总是出现在玻姆轨迹穿过的探测器中……这难道不会令玻姆力学的拥护者欣喜若狂吗?”
争论当然不会就此平息,因为谁都无法直接解释那个最关键的现象——路径探测器记录的路径信息和玻姆轨迹不一致。第一个比较确切的回答见诸克里斯托弗 · 杜德尼(Christopher Dewdney)等人在1993年11月发表的论文《量子轨迹的后测量如何骗过探测器?》。他们指出,不能把干涉仪中的探测器视为孤立的;即使粒子沿狭缝1流过,狭缝2的探测器也会被激发。作者写道:“这是非局域量子势的效应。只需计算就可看出,电子沿一条路径运动并不意味着另一条路径上的探测器不受影响。”1998年,斯库利(ESSW中的第一个S)在《玻姆轨迹是否总能提供粒子运动的可信物理图像?》一文中对数篇质疑ESSW思想实验或支持玻姆轨迹真实性的论文进行逐一回应。针对杜德尼等人1993年的论文,他的评价是“有趣”,但紧接着评论道:“需注意的是,现代物理学中非局域影响的概念绝非玻姆力学的专属。许多终身研究量子力学的学者认为,非局域性是EPR佯谬的固有部分。此类‘非局域性’实际上源于‘共同原因’。例如,EPR实验中的两个自旋均来自同一自旋单态(共同原因),当测得自旋1为上态时,我们‘瞬时’将自旋2投影至下态。但此处非局域的是‘知识’或‘认知’,而这一信息并非以超光速传递。因此,其中并无真正令人震惊的非局域性。”
辩论在各种出版物上延续。一个较为系统的解答于2000年由巴兹尔 · 希利(Basil Hiley)等人在论文《量子轨迹:真实的、超现实的还是对更深层次过程的近似?》中给出。希利是玻姆生前的合作者,与玻姆合著了于1993年出版的《不可分割的宇宙》(The Undivided Universe)一书,书中蕴含的“整体性”思想也在这篇论文中得到体现。希利等人首先赞同了杜德尼等人1993年的论文,并表示ESSW的质疑是源于对正统量子力学的“额外”假设——他们假设能量交换需要满足局域性。更深层地,希利等人聚焦于测量问题,指出哥本哈根诠释要求测量通过宏观仪器的“不可逆放大”来使量子现象“显形”。作者引用了哥本哈根诠释“领头人”玻尔于1935年在《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否可被认为是完备的?》一文中的表达:“任何基本的量子现象,唯有通过‘不可逆的放大行为’将其‘锚定’,才能称为现象。”显然,ESSW的路径探测器不满足这一条件,因此其对能量的测量不能作为路径推断的可靠依据。而玻姆力学通过粒子位置与量子势的耦合,揭示了量子现象非局域性与整体性的本质。马上我们将见到,希利的这篇论文为后续实验考察ESSW思想实验(即考察ESSW设想的探测器是否可靠)打下基础。2005年,列夫 · 威德曼(Lev Vaidman)在《玻姆量子力学中的实在性,或你能用空波子弹杀人吗?》一文中对各种观点进行了回顾。
无论是切实考察ESSW思想实验,还是检验玻姆轨迹的真实性,都需要真正的实验支撑。霍华德 · 怀斯曼(Howard Wiseman)和迪尔分别于2007年和2009年指出,玻姆粒子的速度场与波函数的多维梯度有关,可用弱测量进行实验观察。这里提到的弱测量是一种微妙的测量过程。它不同于破坏性的强测量,而是一种以减少获取信息量为代价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系统演化状态的测量。这种轻微测量可上溯到1979年迈克尔 · 门斯基(Michael Mensky)等人对量子态的连续测量,后被阿哈罗诺夫正式提出和拓展应用。同时,2011年,怀斯曼和迪尔的提议也在沙查 · 科西斯(Sacha Kocsis)、鲍里斯 · 布雷弗曼(Boris Braverman)和西尔万 · 拉维茨(Sylvain Ravets)等人开展的单光子双缝实验中得到应用,相关成果于2011年发表在《科学》期刊上。
基于上述工作,布雷弗曼和克里斯托弗 · 西蒙(Christoph Simon)于2013年在《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发文,提出了一个用纠缠光子观测玻姆轨迹非局域性的实验方案。这一方案被迪伦 · 马勒(Dylan Mahler)等人参考并被付诸实践。实验结果于2016年发表在《科学-进展》(Science?Advances)上,证实了ESSW思想实验所设想的路径探测器是不可靠的,因为其状态会受到非局域影响而发生改变;玻姆轨迹并不像ESSW所说的那样是超现实的。不过,此类实验描绘的是平均玻姆轨迹,并不能直接坐实玻姆轨迹的存在。时至今日,玻姆轨迹的物理真实性仍待进一步实验检验。
玻姆轨迹的另一个重要应用是对双缝干涉实验动量扰动的探究。在双缝干涉实验中,通过探测而获取粒子经过的路径信息,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双缝干涉条纹,这暗示着探测过程中存在对粒子的动量扰动。关于动量是如何传递给粒子的这一问题,已经有研究者进行了多番探讨。2019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肖芽等人利用玻姆力学描述路径探测过程中光子动量的改变量,实验观察到光子在传播过程中动量扰动的非经典累加,首次在实验上验证了粒子动量改变量的平均绝对值与干涉条纹可见度之间的量化关系。实验细节刊登在《科学-进展》上。在文章最后,肖芽等人总结道:“在玻姆力学中将动量视为一种实在要素,可以说是理解路径探测中光子动量变化的最有效方法。此外,这一理论还为部分‘不可控的动量改变’提供了直观图像,从而强化了互补原理:尽管玻姆力学是完全确定性的,但粒子所经历的动量改变取决于其在波函数中的初始位置,而这一位置无法被实验者操控。”
草木百年新雨露:相对论玻姆轨迹中的“非局域能量改变”
2025年,与一项开拓性实验相关的研究成果在《物理评论快报》上刊出,为玻姆力学的研究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篇被选为“编辑推荐”的文章一经刊出就被国内外多个科学媒体争相报道。实验的主要完成人窦建鹏在博士阶段师从金贤敏教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助理研究员,与量子存储实验平台朝夕相处。十几年来,他对双缝干涉实验一直怀有浓厚兴趣。2020年,当时还是博士后的他开始静心思考现在已写进教科书的贝尔不等式。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如同1951年的玻姆,窦建鹏在透彻理解哥本哈根诠释后,迫切期望更深入地了解量子现象的本质。经过调研,他很快就被玻姆力学清晰直观的表述吸引。在看到ESSW和杜德尼等人的两篇论文后,他惊讶地发觉自己每天实验用到的量子存储器,竟然与ESSW所提到的路径探测器十分吻合。
如上文所述,ESSW要求探测器在不扰动粒子运动的情况下,记录粒子的路径。而量子存储可以产生量子态(这一过程会产生S光子),并将其保存在原子中。实验者可以等到合适的时机再将量子态“取出来”(这一过程会产生A光子)。如果让两个量子存储器产生的单个S光子在后方进行干涉,不就相当于双缝干涉实验了吗?而S光子究竟是两个量子存储器中哪一个产生的(相当于双缝实验中粒子经过了哪一条缝),可以通过对A光子的探测知道——如果某个量子存储器在一定时间后产生(不产生)A光子,那S光子就是(不是)从它发出的。得益于量子存储可将量子态保存一段时间,在实验中等到S光子已经穿过干涉区域并被强测量后,再从量子存储器中“取出”A光子,就可以在不扰动S光子演化的情况下知道S光子走了哪条路径。这甚至比ESSW所设想的路径探测器还要完美——后者只要求对粒子的运动状态无显著影响,而前者在理论上可以不施加任何扰动。
除此之外,使用原子保存路径信息还有其他妙处。杜德尼等人在1993年指出,量子系统的能量分配可能会以非局域的方式发生变化。这不仅不能用能量的局域“传输”来理解,而且不能用“正统方法”(即哥本哈根诠释)做到。但是,当时的研究者苦于没有如此理想的路径探测器而不得不止步于此。在进行实验前,研究团队受其启发提出了“非局域能量改变”的概念。它并非能量的超光速传输,而是通过量子非局域性在类空间隔范围内对能量分布进行调整。而发出S光子的那个量子存储器,其能量要比另一个量子存储器略高。直觉来看,能量并不会从一个量子存储器中突然消失或产生。但是在非局域影响下,这部分高出的能量可能会在两个量子存储器之间发生转换。“非局域能量改变”这一新奇概念竟可以如此自然地在量子存储实验中得到检验!
然而,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考虑。为了把隐变量纳入体系,研究团队将能量的空间位置指定为隐变量。除了普通的强测量,他们还使用了特殊设计过的弱测量。这类似于一个视线受阻的观察者在查看哪个量子存储器中的原子被激发了。观察者仅对量子存储产生轻微扰动,同时获得一些关于能量位置的模糊信息。这些位置信息可以与后选择操作一起,验证过去发生的事件和未来发生的事件之间的量子关联。通过比较各种概率的实际测量值,就可验证“非局域能量改变”究竟是否切实发生。一切看上去并不难。
两年后,实验完成了。然而,ESSW设想的是原子干涉,研究团队实施的是光子干涉。光子是一种相对论粒子,这导致他们不能采用非相对论理论来描述自己的实验。此前,将德布罗意-玻姆理论推广到相对论范畴的尝试已然很多,包括玻姆本人也于1953年进行过类似尝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尝试并未取得成功或被广泛认可。因缘际会,和合而生。就在研究团队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之际,一篇2022年发表在《自然-通讯》(Nature?Communications)的文章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在这篇文章中,约书亚 · 傅(Joshua Foo)等人从“操作主义”(即通过物理测量来锚定现象本质)的角度出发,利用弱测量成功构建出相对论玻姆速度和玻姆轨迹。正是得益于此,研究团队计算出符合实验配置的二维空间加一维时间的相对论玻姆轨迹。他们发现,自己的实验结果与非局域理论的预测一致。最后,他们总结道:“在德布罗意-玻姆理论的框架下,由于两个纠缠粒子的非局域量子关联,一个粒子所携带的能量可以在另一个粒子的影响下发生非局域改变。?”
二维空间加一维时间的相对论玻姆轨迹
这项工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了令玻姆力学再一次被学界重视,量子存储也凭借该工作跃上量子力学基础研究的舞台。此后,量子存储或将继续为基础量子问题的检验提供有效帮助。至此,玻姆力学的故事告一段落。从1927年导航波理论,到如今的非局域能量改变,德布罗意-玻姆理论经历了波谲云诡的九十八年,其间亦有不绝如缕之处,如今可谓天光乍泄。珠玉在前,怀璧其后。笔者坚信,在量子技术蓬勃发展的同时,将会有更多研究者开始关注量子力学基本问题。最后,笔者使用DeepSeek以“量子非局域”为题赋诗一首,以飨读者:
量子深阁探幽渚,玉匣轻鸣罢旧符。
光痕朝引微澜渡,云幕夜收玄雾图。
虚波叠影时难驻,能易空移几度秋。
导航遗策今犹在,域外长河涌新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文作者尚晓文是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金贤敏教授课题组博士生;窦建鹏是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唐豪是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教授;金贤敏是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